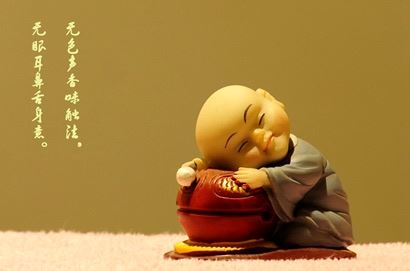
公案颂古与本原心性
二、本心的迷失
吴言生
[台湾]东大图书公司,《经典颂古》,2002年11月初版
第4753页
对本心迷失的反省构成了禅宗哲学迷失论的内容。禅宗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、不觉、缺撼、执着的状况及缘由。禅宗认为,人的本来面目清纯无染,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,人们逐物迷己,迷己逐物,从而导致了本心的迷失。禅宗公案和颂古,从各自的角度表现了对迷失的反省。在《颂古百则》中,表达对本心迷失思考的公案较少。这是因为禅宗公案注重揭示本原心性的超越质性、注重揭示顿悟成佛的不二法门、注重揭示内证绝言的禅悟境界,而对本心为什么会迷失这样一个学理性较强的问题,则较少注意。在为数不多的与此相关涉的公案中,也仅是指出本心迷失这一事实,而不过多作理性的思考。而禅之所以为禅,其特色也正在这里。
1.逐物迷己
追逐外物,从而迷失了本原心性,这是禅宗的基本看法。表达对本心迷失之反省的,有镜清雨滴公案及颂古。《碧岩录》第46则:
镜清问僧:门外是什么声?僧云:雨滴声。清云:众生颠倒,迷己逐物。僧云:和尚作么生?清云:洎不迷己。僧云:洎不迷己,意旨如何?清云:出身犹可易,脱体道应难。
本则公案中,镜清明明知道是雨滴声,却问学僧是什么声音,这种机法,如同探竿影草,旨在考验僧人的悟境。僧人随着舌根转,说是雨滴声,可谓贪他蓑笠者,失却旧茅亭(同上长灵卓颂)。殊不知,轩檐水玉,原系己身,若是真正无心,臻于放弃一切妄想的省悟境界,则所听到的屋檐下雨滴声就是自己,在这种境界里没有自己与其他的对立。此时,会有好像自己变成雨滴的感觉,不知道是自己滴落下来,还是雨水滴落下来,这就是雨水与自己成为一体的世界,也就是虚堂雨滴声所表现的世界。自己与雨滴声合而为一,就是无心的世界。听到雨滴声,并与雨滴声合为一体,是超越经验的纯粹经验。
由于僧人站在物我分离的立场上回答是雨滴声,所以镜清予以批评。学僧反问镜清如何体会,镜清说:等到能不迷失自己的时候就会明白。学僧仍然没有领会,镜清便入泥入水,对他说:出身犹可易,脱体道应难。突破身心的牢笼,从这个迷惑的世界超脱出来还容易,要想使道体透脱出来就困难了。所谓使道体透脱,就是使道体从其安住的超悟之境再脱离出来,重新回归于这个声色纷纭的现象界。如果停留在绝不迷惑的小乘罗汉境界里,是绝对不可能解脱的。必须和光同尘,使自己觉悟的光明柔和下来,与众生迷妄颠倒的迷惑世界打成一片,还要以最好的方法表现出自身的了悟境界,去教导人们。(《一日一禅》第216页)雪窦颂云:
虚堂雨滴声,作者难酬对。
若谓曾入流,依前还不会。
曾不会,南山北山转滂霈。
虚堂雨滴声之所以使得深谙禅理的行家也难以酬对,是因为如果你唤它作雨滴声,则是迷己逐物。但如果不唤作雨滴声,它不是物,你又如何转物?若谓曾入流,依前还不会。仍用《楞严经》意旨:初于闻中,入流亡所。所入既寂,动静二相,了然不生。这是《楞严经》里观世音菩萨的音声入定法门,听一切声音,听到入流(进入法性之流),亡所(所听的声音听不见了),所入既寂,声音寂灭了,清净到极点,然后,动相(一切声音)、静相(没有声音),了然无碍,一念不生。雪窦说,纵使到了这个境界,也仍然没有进入禅的大门。结句以南山北山转滂霈,形容越来越大的雨滴声,以及听雨者能所俱泯、即心即境的直觉体验,可谓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。
雪窦此诗先以虚堂雨滴声,作者难酬对。若谓曾入流,依前还不会点出檐前雨滴公案机锋的陡峻,连行家也难以酬对。再运用楞严三昧和金刚般若入诗,若谓曾入流潜蕴着入流亡所的楞严三昧,禅心幽秀,悟入玄微;而依前还不会的金刚般若,则又将之扫却,从而使禅悟体验跃入新的层面,上升到绝巅至极之处,不立文字,言亡虑绝。最后用现量境作结,提示道曾不会,南山北山转滂霈,指出只有能所俱泯,才能充分体证到南山北山转滂霈的现量情境。
2.自昧本来
本来面目净裸裸赤洒洒,显发着无穷妙用。由于受到了客尘的障蔽,致使人们不能认识它,不能直下承担,使之显发大用。象征本心迷失的,有盐官犀扇公案及颂古。《碧岩录》第91则:
盐官一日唤侍者:与我将犀牛扇子来。侍者云:扇子破也。官云:扇子既破,还我犀牛儿来。侍者无对。投子云:不辞将出,恐头角不全。石霜云:若还和尚即无也。资福画一圆相,于中书一牛字。保福云:和尚年尊,别请人好。
禅宗时时刻刻以究明本心为念。本则公案中,盐官以犀牛扇子作为象征,为的是让人们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资福在圆相中画牛字,即是提示犀牛扇子系指大全自性,而非指作为实物的扇子。雪窦颂云:
犀牛扇子用多时,问着原来总不知。
无限清风与头角,尽同云雨去难追。
犀牛扇子用多时,问着原来总不知。每个人都有一柄犀牛扇,在生命的时时刻刻,都仰仗其发挥作用,它是生命的本原。但当师家询问它时,学人却并不知道自身本具。两句感叹世人逐物迷己,只知道追寻外物,却不知道自身本具的犀牛扇、玻璃盏。
无限清风与头角,尽同云雨去难追。因为人们不识本有的佛性,不识自性的犀牛,于一问之时懵然不知,从而使得犀牛扇子的无限清风,随着头角峥嵘的犀牛一道,如同云飞雨逝般一去难追。反之,如果知道人人本有的那一柄犀牛扇,在一问之时,就用不着去管什么扇子,只须做个摇扇的动作,就可以使人顿时感受到清风习习,宇宙清凉。
此诗前二句通过对公案的品鉴,表达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感悟。三四句以清风、头角,双绾扇子与犀牛,并将之与易逝难追的云雨相类比,生动形象地传达出对世人不识本心的惋叹之情。

